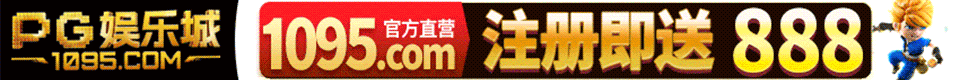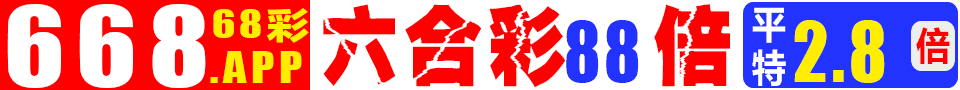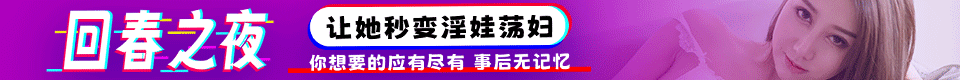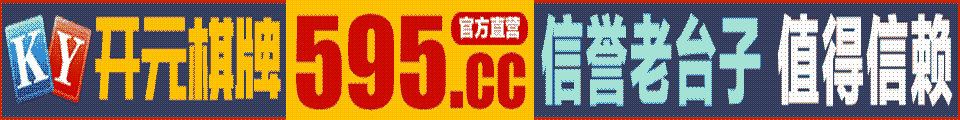沧海孤艳(上)
沧海孤艳
(一)
已经是中午了,虽然在冰天雪地,也因为承受的阳光而透出几分暖意。“啾啾!”
几只小鸟,弹落了枝头的积雪。
一栋藏在积雪下的木屋的门打开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伸出头向外探看后,熘出门外。
他脚上穿着厚厚的乌拉,这是东北的“三宝”之一,厚厚的皮毛上衣,敞着领口,露出结实的肌肉,他手里提着木桶和一把生锈的大柴刀。
“阿雄,不要走远了。”
就在他离开木屋的时候,屋里有一个女人声音喊到。
阿雄的全名叫苟雄。
“老妈,你放心,我就在前边的小河上。”
苟雄他应了一声后,像一头豹子,纵越过雪地,向前奔去,对于覆盖在雪下的丘壑路径,他熟悉得连看也不用看。
苟雄沿着盈雪的山脚,直奔结冰的小河而去,来到结冰的河面上,把水桶放在一边,就用柴刀砸冰。
冰层很厚,他不断的往下挖着,一下也没偷懒。
“咚”的一声。从冰下溅起了水花。
“嘿嘿!”苟雄咧开大嘴,高兴的笑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鱼线,装上饵,小心的垂进冰下的溪水里,充满希望的期待着。
一次又一次,他满怀希望的提起钓线,可是一次又一次,带给他的是失望。“我X,真倒霉!”“饵又被吃了!”苟雄又再次装上饵,他微笑的脸上充分显示出信心。
“呦呵——”
终于,他惊喜的叫起来,细细的线上钓起一条约一尺来长的鲤鱼。
鲤鱼在冰床上跳着,苟雄傻傻的笑着,一双大眼睛,瞪着那条挣扎的鲤鱼。“哇塞,爽!”他立刻取下鲤鱼,重新上饵,正要垂下冰洞时,忽然从远处传来马蹄声。苟雄惊惶的眼神,不住的四处打量寻找着。
“嘀哒、嘀哒……”蹄声越来越近,苟雄不由得站起身来。
一箭远的山头上,出现了三条身影,他们正策马扬鞭的急奔而来。
瞬间,他们已到了河岸边。苟雄手拿着鱼线,用脚踏着钓上来的那条鱼,惊疑的望着三名马上客。
一个独眼的魁梧大汉,摘下头上的四块瓦帽子,扇着风,向苟雄问到:“小兄弟,这里就是白头山吧!”
苟雄不答反问道:“你们要找谁?”
他看到独眼汉,满脸的虬髯,一脸的凶相,心理直犯嘀咕,眼睛不禁的朝地上的柴刀看。
“哇操,万一有什么,就给他一刀。”
独眼汉子回答到:“我们是来采参的。”
苟雄这才道:“采参的有很多家,你们找那一家?”
“听说姓‘苟’”
苟雄怀疑的问到:“苟什么?”
“苟旦!”
苟雄打量着三人,昂首回答道:“那是我老爸,你们找他干什么?”
独眼汉子朝一个瘦鬼说道:“马猴,你来告诉他!”
瘦鬼舔了舔嘴唇,朝苟雄解释道:“小朋友,咱们是参行来的,听说你老爸这趟采到‘棒槌’了,怕他开春出手给别人,所以特来向他订货的。”他说话的声音又粗又哑。
苟雄见过不少参行的人前来定货,不过,都出不起价钱,据他老爸说,这趟采到的“棒槌”,可以卖很高的价钱。“多高啊?”他记得自己曾经问过老爸。苟旦得意的笑道:“阿雄呀,这次下了白头山,以后咱们就在也不用到这冰天雪地的鬼地方来吃苦受罪了。”
所以,他希望这三个人是出的起价钱的“大头”。
苟雄转身一指道:“拐过了那边,有一栋小木屋就是啦!”
马猴吆喝另一个四十来岁,皮肤黝黑,身材结实的汉子道:“黑狗,你的鼻子管用,你走在前面给当家的带路。”
苟雄鸡婆的说道:“顺着我的脚印走,包你们能找到小屋。”
黑狗“哈哈哈”大笑的说:“小朋友,忙你的吧!我们来白头山采参时,你还没出娘胎呢!”
言罢,三人策马而去。那爽朗的笑声还回荡在空旷的山野中。
“哇操,我右眼皮怎么自动跳起来了?”这时苟雄的心里忽然不安起来了,那三个人的的容貌、举止;清晰的印在他的脑海里。“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哇操!不行,我得赶回去看看!”
苟雄正要赶回去,他拉起垂在冰河里的钓钩。忽然,手中感到沉甸甸的,一种有力的挣扎,很快的震撼了他的心。
“哇塞,又钓到了!”
他拉起第二条鱼,比原来的那条鲤鱼还要肥壮。他登时忘记了那三名参客的事。
银白色的大地,反射着刺眼的阳光。苟旦站在木屋前晒着太阳,憧憬着未来的幸福生活。采参者最高兴的梦想,他现在已经实现了。苟旦不会轻易脱手,因为那一对棒槌是他们一家的希望。他知道着棒槌若拿到城里去,知名的参行,都会来找他收购。因此苟旦不想在这里脱手,反正已经苦了几十年,又何必在乎到明年春天呢?
“嘀哒,嘀哒……”
三匹马向木屋走近时,他已知道对方的来意。
他们在木屋前下马,独眼汉子扬声道:“喂!你就是苟旦,苟爷吗?”苟旦问到:“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独眼汉子回答道:“我们是参行来的,这趟路真辛苦,进屋说吧!先弄碗水喝!”他们三个反客为主的不请自入。苟旦也跟了进去,又问:“你们是来买参的?”
“不买!我们从来不买任何东西,我来替你们引见引见,马猴、黑狗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独眼汉子脸上带着一丝笑意,沉声说到。苟旦见他们说话根本不像生意人,心里有些不高兴。
“那你呢?”
“独眼刁”
“独眼刁!”
苟旦曾去过长春,虽然没遇上,却也听说过,胡匪里头有那么一个独眼刁。如今遇上了跑也跑不掉,苟旦强持镇定。
“久仰大名!不过,我这里没有各位要的东西。”
“谁说没有?”
苟旦怯声说道:“你们知道,冰天雪地里不出参。”
独眼刁摸摸胡子说道:“我们不要参。”
苟旦不解的问:“你们不要参,你们要什么?”
独眼刁笑答道:“要你的采参图。”
“啊!”苟旦神色慌张的望向墙角,独眼刁这时已暗中注意到。
“哼!”“我看我还是自己拿吧!别劳您大驾了!”言罢,独眼刁往墙角里走。苟旦既愤怒又惊慌的喝道:“你想干什么?”
“乒乒乓乓!!”他赶上去拦阻,被黑狗伸手扯着,轻轻一带,摔在屋角,撞倒了屋里是桌椅。
“哎哟!”他挣扎要爬起来,马猴和黑狗已经拔出刀,架在他的脖子上。“阿雄他爹,你在做什么呀?”
苟旦的妻子被着响声,惊赫得从屋里的小门慌慌张张的冲进来。一看到此情景,她惊得呆住了!
独眼刁拿下那张采参图,展开一看,得意得大声狂笑:“哈哈!”
“强盗、土匪……”苟旦不顾一切的冲上去抢,黑狗挥刀向他身后砍去。“啊——”苟旦惨叫一声,扑到在地。
他的妻子扑上去,放声喊道:“阿雄,快来呀!你爹被人杀了……”
马猴立即冲上前去捂住她的嘴,阻止她喊叫出来。看到自己的丈夫倒在血泊中她悲痛欲绝!同时她感觉到一双的大手便往她的胸前袭去,“咧”的一声,没两三下便把她的上衣脱了个精光,露出两颗肥大雪白的奶子,然后双手由内而外的搓揉着,拇指并食指轻捏着乳尖。
“杀了我,杀了我……”那女人大叫。
马猴此时一边脱她的裤子,一面淫笑道:“别催呀!我会‘杀’了你的,嘻嘻!”此时她的双手双脚,被压得无法动弹,仅能的是摇头哭喊。
“不,不要……”
(二)
此时马猴已经褪下她的裤子,女人茂密的阴毛与神秘的私处顿时一览无遗。丈夫已遭杀害,自己又将受辱,此刻的她,整个都快疯了,如果不是儿子还在,她一定会咬舌自尽。
“阿雄,阿雄……”她高喊着儿子的名字,可惜儿子还没回来。
这时她被摁倒在地上。两只又长又大的手掌,紧紧攀附在两团白皙浑圆的乳房上,死命的左搓右揉着。
“啊——!”她张口唿叫着,也不知是痛还是爽?!“唔……不要……我……”
只见马猴拉下裤子,露出了那根充血发硬的肉棍,然后对准花瓣的中心,摒足腰部的力量向目标插入,女人眼里含着泪水,却只能看着肉棒从龟头开始,一点一点的没入自己的花瓣内,直到整只火热的肉棒都插入自己体内。
“马猴,加油呀!”旁边有人乐道,女人只感觉到有根铁棒戳进自己体内。由于没有前奏,肉穴内十分干燥,这滋味不怎么好受!
可马猴不管这些,只管自己撅着屁股,不停的的在抽送自己的肉棍。
马猴每一次抽插都会竭尽全力的把阳具插到最深处,肥大的龟头回回都顶到子宫最深处的花心。温暖的小穴紧紧的含住了火热的铁棍,滚烫的高温在阴户里燃烧。粗大的阳具在窄小的阴户中摩擦,乳白色的淫液随着摩擦的加剧不断的从肉棒和小穴的结合处被挤了出来。“啪啪……啪啪……”肉碰撞在一起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了。
“你这土匪……哎呀……呜呜……”
“哈哈——”马猴的手在肉棒抽送的同时,不停的在女人乳房上一会儿揉,一会儿压,同时也用嘴去吸。
吸、嘬、拉、扯;好像要把奶头拉掉似的。女人丰满的乳房在他双手的蹂躏下,不停的变换着形状。女人感觉到既酥又麻,紧闭双眼,任由马猴粗大的肉棒在小穴中一次次如同打桩般的抽插。除了鼻息越来越急促,她也要守住女子最后的坚持,她决不要像一个荡妇那样的辗转哀鸣,呻吟求饶。
马猴一口气干了七八十下随即大声一吼,已经胀得巨大无比的肉棒里冲出了火热滚烫的精液,喷洒在了女人的花心。
“换我来!”黑狗见他泄了,自告奋勇去接手。只见他把女人的两条修长白皙,但却沾满了淫液的双腿呈V字型的大大张开,扛在自己的肩上。再次将阳具戳进了阴户。
“啊……啊啊……呜……呜……”这次插入的肉棒竟然较之前的几次更为深入,大龟头紧顶花心,直叫她喘不上气来。女人肥美的臀部整个儿的抬在空中,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曲线。
但是白皙浑圆的大腿却被黑狗的双手紧握着,并且拉开成了大大的V字。茂密的芳草中那一朵娇艳欲滴的花蕾绽放开来,高傲的挺立着,接纳着雄壮阴茎的奋勇冲杀。黑狗太久没有“吃肉”,所以并不懂得怜香惜玉,干得她又红又肿,一副生不如死的模样。
“……啊,啊……啊……啊哟……不要啊……”女人颤抖着的呻吟声和着低婉的哀求声回荡在卧室中,肉体交和时阴户与阳具撞击的“噼啪”声不断的冲击着弥漫在小屋里。
“加油呀,加油!!”
女人只觉得耳畔的声音越来越小,也越来越远。直到什么也听不见……“红姑娘子结大桃,老鼠背着大老猫。蚊子下了天鹅蛋,打破了,管来验。吹喇叭,打行锣。鞍子背到牛尾巴。”苟雄提着战利品,唱着小曲,欢欣雀跃的回来了。他现在的喜悦不亚于他爹几十年前,第一次采到参。
“老妈,老妈!”
人还未到他老远的高声唿喊着。苟雄奔跃到木屋前,方才觉得怪异,为什么寂静得这么可怕?
他不由得想起不久前,来过的三个人,心底不禁一惊,放声狂叫:“老爸,老爸……”
木屋没有回应。“砰!”他突然扔掉手中的木桶,任水流满地,鱼也满地乱蹦。苟雄三脚并成两步,飞也似的冲进屋里。
“啊!”一片血迹,进入了他的眼帘,他怔住了!
“老妈!”他扔下了柴刀,疯狂的冲到母亲身边,他娘早就气绝身亡了。身上一丝不挂,大阴唇依旧还是朝着两边湿淋淋地翻着,根本没有合拢。阴毛上、肉洞口、大腿上到处都煳满了混合着精液和血迹的液体。
“老妈,您醒醒,醒醒呀!”他声嘶力竭的喊着,可惜他的母亲依然没有反应。苟雄失望的抬起头,有看到近处的老爸,他爬过去,悲痛欲绝的喊着:“老爸!”
“呜呜——”他跪在地上,泪如泉涌。
突然,他发现父亲的嘴唇在动,似乎在说什么,他又燃起一丝希望。苟雄急忙把耳朵贴上去,吃力的听出来了,“是独眼……独眼刁干的!”
“独眼刁干的?”苟雄又问了一次。苟旦勉强的点了点头。然后头一歪就死了。
苟雄茫然的站在屋里。他不知独眼刁是何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忽然,他又想起那三个人,苟雄第一眼看到他们,就留下了邪恶的印象。他不由得想起了采参图,那是他老爸在各处寻参时加了苟家的记号,按照采参的规矩,就是他们的了,只等到开春解冻,在按照那图去挖取。他忙跑过去去找,空空的,采参图早已不见了。“哇操,是他们没错!”
他忿恨的捡起柴刀,飞快的冲出门外,在屋后的雪地上,清晰的留下一片马蹄踏过的痕迹。他们三个人,是走后山小路跑的。苟雄迈开脚步随着蹄印追了下去。
“唿——唿——哇操!”追出了一里多地,仍不见踪影,他气喘如牛。天慢慢的黑下来了。苟雄赶了半天的山路,感到有点饥肠辘辘。而且,黑夜在山路上行走非常危险。尽管他心中焦虑,却也不愿冒这个险。因为一旦自己完蛋,这笔血债就无人讨了。转过山坳,出现了猎户的古屋。
冬天以来这里是空的,他曾经来过几次。苟雄在古屋前停下来,撬开古屋的锁,走了进去。屋里要比外面暖和得多。这时他才想起,临行前忘了带干粮。“唉!”苟雄不由得叹气,人在悲痛时,总是会顾此失彼的。他先掩上门,寻找了一下,好歹在屋里虽然没留下吃的,却有干柴,可以起火来取暖。“咕噜,咕噜……”苟雄生起火后,身子暖和起来,肚子反而更饿了。他找到一把茶壶,出去弄了点雪,放在火上想把它烧开,喝点开水,也许能稍微止住点饥饿。
“嘀哒,嘀哒”正当水壶响的时候,意外的传来了马蹄声。数匹马凌乱的蹄声,给苟雄带来了希望,他暗自想到:“难道是那三个家伙也来到这里了?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啊!”
“啪啪”蹄声近了,有人在室外下马,脚步声朝古墓过来了,苟雄的心情既兴奋又紧张。
他跃身到屋角的旧木橱后面,手里紧握着那把柴刀,胸膛燃起复仇的火焰,一双眼睛死盯着古室掩住的两扇门。
(三)
“呀”古室的门徐徐的被人推开,火光映着进来人瘦小的身影,他的帽檐压的很低,看不出整个容貌,只能看到他那棱线分明的嘴唇。
苟雄不认识他,但是却可以肯定不是自己的仇人,那人看了屋里一眼,背对着苟雄在火边坐下来。
壶里的水开了,他仿佛在自己家里一样,先从桌上拿起了碗,倒上开水,然后,放下肩上的褡裢袋,取出一块干粮,泡在开水里,斯斯文文的吃起来。苟雄看到直流口水,刺激的他越发难受,肚子里的饥肠叫的更响。他忍不住的悄悄走出。蹑着脚到了那人身后,把生锈的柴刀一横,陡然的架在那人的脖子上。
“不要动,动,我就杀死你!”
那人微微一怔,从容的说道:“你要干什么?”他的声音清脆而细柔,足以消除一切的敌意。当然苟雄也不例外。因为他本来就没有敌意,激动的声音平静下来。随即说道:“把干粮给我吃!”
那人背着身子,把手里的干粮送给苟雄。
苟雄接国干粮,那人把腾出的手,轻轻的推开苟雄的刀,说道:“我本来就不想杀你,单你手里拿着刀,就不能不防着别人要杀你”。说话间,陡然回手一掌,把苟雄打的站立不稳,向后直退,终于靠在木橱上。
苟雄惊愕之余,赫然看清那人,长的眉清目秀……却没有半点男子汉气,惊讶的问道:“你是女人?”
“是。又怎么样?”
那人说着摘下帽子,披下一头乌黑亮泽的秀发,嫣然一笑道:“我是女人,难道不行吗?”
苟雄见她并无恶意,就说道:“哇操!你是女人我虽然有点意外,但你却一掌把我打在这里,让我吃惊!”
女人听到这里说道:“我早就说过,既然拿着刀,就不能不防着你。”苟雄答道:“我看你也是无心打我,咱们又无怨无仇的,周围只不过朝你要点吃的罢了。”
“你叫什么名字?”
“苟雄……”话声未落,她就忍不住噗嗤笑了。
“哇操!有什么好笑的?我姓的苟可不是狗熊的狗!”
“哦!我懂了!”她恍然大悟那你呢?
“我叫金花”
“你一个姑娘家,大冬天道山里做什么?”
金花脱下灰色的外衣,露出一身大红的紧身短衣,英气逼人的说道:“跟我爹进山来捕貂。”
“哦!”苟雄应了一声,哀伤的低下头。
“你怎么了?”金花关切的问道。
苟雄不禁垂泪回答道:“我老爸、老妈不幸遇害,我是寻仇家的。现在连你也打不过。看来仇真的报不了了!”
“你的仇人是谁?”金花问苟雄。
“独眼刁。”
金花闻言说道:“他可是土匪里最凶的一个。”
苟雄问道:“他武功怎么样?”
金花笑道:“足够收拾你。”说完,她扔了一块干粮给苟雄。
苟雄接过干粮,两人在火边坐下来。金花俏丽的面容被火映得红红的,越看越美,苟雄不由得看傻了。
她有点不好意思,低下头道:“你这样看人家做什么?”
苟雄忽然站起身,正色的问道:“你知道独眼刁?”
“当然知道!”
苟雄又问道:“他的武功比你强吗?”
金花笑着回答道:“如果我要找他寻仇,八成他死定了!”
“扑通!”的一声。苟雄闻言后立即双膝一曲,跪在金花面前。
金花大吃一惊道:“你这是做什么?”
“我要拜你为师”,他神情严肃的说,一点也不像在开玩笑。
金花险些笑出来,拉着他说:“你别跪在地上,起来说话好不好?”
苟雄坚持道:“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了!”
金花想了想道:“好吧!,我问你,你今年多大了?”
“17岁零1个月。”
金花又反问道:“你知道我多大了吗?”
苟雄摇摇头。
金花道:“明天我才16岁。”
苟雄连磕三个头,恭敬的说道:“弟子先给师傅请安!”
金花又“噗嗤”笑出声来,说道:“你听说过,16岁的师傅收17岁的徒弟吗?”
“有!”
“说来听听。”
苟雄正经说道:“就是你和我。”
“别瞎闹,赶快起来吧!”
苟雄认真的说:“你不答应收我做徒弟,我就是死也不起来的。”
“当真?”金花被他的诚心所感动。
苟雄点头道:“对!”
金花沉思片刻后,慨然回答道:“好吧!”
苟雄欣喜的说道:“你答应了?”
金花摇着手,说道:“我可没答应你什么,不过看在你一片诚意,我可以找一个人给你做师傅,他的武功比我强十倍。
“那人是谁?”苟雄急忙问道。
金花一边吃着干练一边喝着水说道:“起来等着吧,一会儿他就来了。”苟雄不言不语,还跪在那里。
金花催道:“起来呀!跪上瘾啦!?”
苟雄喃喃的说道:“既然一会儿到,我还是跪在这里等好了。这叫做……”他挠了一下头,皱着眉想问下一句话。
金花等得不耐烦,忙问道:“叫做什么?你快说出来呀!”
“叫做……”
他想了半天,忽然兴奋的说道:“这叫做‘不到黄河不死心’。”
金花忍不住“扑哧”一笑,吃在嘴里的东西,全都喷出来了。
“呀!”
屋门忽然开了,一个健朗的老者出现在屋子门口。
(四)
他那双眼睛炯炯有深,爽朗的向金花说道:“阿花,天这么冷,你怎么把牲口扔在外面,存心想冻死它呀!”
金花站起身说道:“我也是刚刚到。”
老者把冷厉的眼神,投到跪在地上的苟雄身上,诧异的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金花笑盈营的说道:“爹,这是您的大喜事!”
“什么大喜事?”
金花的小嘴一奴,说道:“爹,他要拜您为师……您要收徒弟了!这不是喜事吗?”
老者严肃的说:“胡闹!那个不知道,我‘金喇叭’从来不收徒弟!”金花接口说道:“我早就告诉他了,可他偏偏不信。”
金喇叭仔细打量着苟雄,然后问金花道:“这小子叫什么名字,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他叫苟雄,”金花双手一摊,道:“可不是我认识他,是他这把刀找上我的。”
说完,她踢着丢在地上的的那把生锈的柴刀。
金喇叭掩上屋门,坐下来问苟雄道:“小伙子,有什么话起来说。”
苟雄闻言后坚持的说道:“您不收我做徒弟,我宁愿死也不会站起来的。”金喇叭考虑了一下,然后说道:“那你就跪着讲吧!怎么回事?”
“是!”
苟雄把自己的遭遇,细说了一遍,捡起那把生锈的柴刀,狠狠地说道:“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他们,为死去的父母报仇。”
“起来说话!”
金喇叭说话的语气含着无限的威严,使苟雄失去反抗意志,徐徐的站起来,完全慑服在对方的威严之下。
金喇叭沉声向他道:“你要学的,不是武功,而是要站起来,在任何地方、任何人面前,都要两腿有力,稳稳的站住。”
苟雄恭谨应着:“是!”
金喇叭坦诚的道:“小伙子,你的遭遇的确令人同情,你的雄心值得表扬,你的孝心也很可佩,不过,我要告诉你,我还是不能收你做徒弟。”
苟雄又要跪下。
金喇叭厉声说道:“阿雄,你又忘记了,第一件要学的事啦?”
“是!”
他重新站好,注视着金喇叭。
金喇叭慢条斯理的说道:“你第二件要学的是不管做什么,最重要的是先保住性命,你立志报父母之仇没有错,但是不能先丢了性命。”
“哇操,你们把我当疯子啦!”
苟雄大叫着跳起来,倒把金喇叭父女吓了一跳。
金花望着他那可笑的神情说道:“喂!苟雄,你在发什么神经呀?”
苟雄说道:“那要问你们呀!”
“问我们什么?”金花一脸不解的神情。
苟雄挥舞着结实的手臂,气唿唿的说道:“哇操!我要找仇家为父母报仇,你们说我没本事;我要拜你做师父,你们又不收我做徒弟;我要找他们一拼,你们又说要我不要去送死,那到底要我怎么办?”
金喇叭望着苟雄发飚,暗自好笑,望着金花道:“这小子是在埋怨我们?”金花道:“他说的也又道理。”
金喇叭走过去拍着苟雄的肩膀说道:“傻小子,出去把牲口带进来。”苟雄欣喜的说道:“你答应做我师父啦?”
金喇叭立刻绷起脸严肃的说:“门都没有!不过,我答应让你跟在我身边,直到我认为你又能力找独眼刁报仇。”
苟雄楞楞的看着金喇叭。